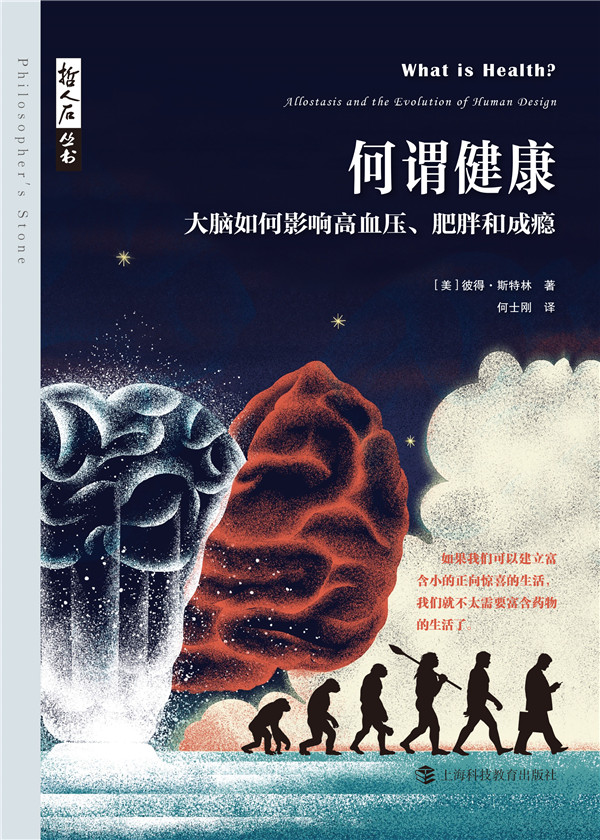
对本书的评价
◇
彼得·斯特林是一位卓越的神经科学家,他在应变稳态方面的工作推动了对我们的大脑及其功能结构的理解。《何谓健康》延续了深刻的学术工作,并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提供医疗服务及如何培养下一代医疗服务从业者。
——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Katrina Armstrong),
麻省总医院院长
◇
这个关于人类身体之智慧及我们控制身体手段之贫乏的明晰故事,对在当下个人和星球的危机中如何过好我们的生活具有深刻的提示。一个对智人绝妙且忧心忡忡的致敬。
——托·诺润川德(Tor Nørretranders),
《用户幻觉和慷慨之人》(The User Illusion and The Generous Man)的作者
◇
这个出色且有远见的神经科学家从现代生活的喧闹和混乱中跨离了一步,回到了第一原理。他提出,我们应该以脑功能定义我们的目标,并作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政治决断和经济决断。当正确理解时,大脑告诉我们什么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然而我们有时未经思辨的选择会将我们引向错误甚至致命的方向。一本精彩和重要的书。
——沃尔弗拉姆·舒尔茨(Wolfram Schultz),
剑桥大学教授,2017年大脑奖获得者
◇
彼得·斯特林带领我们对自身的历史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巡视,从单个细胞到智人的演化。理解身体对环境适应的方式会产生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洞见。你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审视疾病、成瘾和健康。
——基思·佩恩(Keith Payne),
《损坏的梯子》(The Broken Ladder)的作者,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系教授
作者简介
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出现在20万年前。带着火、简单的工具和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我们迅速占据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如今,尽管我们拥有极其先进精良的工具,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却威胁着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许多人失去了生活的欲望,迷失于酒精、过度饮食甚至自我伤害,我们中的有些群体甚至面临着总生育率跌落至远低于维护人口稳定所需的水平。我们为何沦落至此?未来将何去何从?
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我们需要从个人身体的最基本层面到社会大环境,去全面审视“何谓健康”。自然选择将每个生物体设计得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资源。我们的大脑预测未来的需求并调控代谢、生理和行为,以确保“恰到好处、及时足够”地递送身体所需的能量与物质。这就是所谓的“应变稳态”,毕竟,预防出错比改正错误更能节省能量。预测调控需要通过学习来实现,为此,大脑用一个脉冲的多巴胺(它使我们体验到一次短暂的满足感)奖励每次正向的惊喜,以鼓励学习行为。
然而现在,获得食物和舒适感不再是惊喜,我们被剥夺了日常小奖励——维持积极行为和良好情绪的基础。由于缺乏日常小惊喜,我们坐卧不宁,只能通过消费寻求新的奖励:比如用暴饮暴食、滥用药物等来刺激多巴胺大量释放。在这种情况下,身体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才能感到满足,最终,我们不仅常常高血压、肥胖傍身,还容易陷入成瘾的泥潭。
当前标准医疗手段是通过阻断奖励机制来治疗成瘾,但这个策略起效的同时,也阻碍了满足感的获得,甚至加深了绝望。当前标准经济学理论指出要促进“发展”以提供更多“就业”,但缺乏挑战、缺乏满足感的工作并不能帮人们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作者强调,为了恢复健康,我们需要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去扩展获得小满足的机会,从而拯救奖励系统,避免其陷入病态。
中文版序1
何士刚教授最近的译作付梓在即,嘱我为之作序。 该书作者是我熟悉的视觉研究的大家彼得·斯特林(Peter Sterling),他向以对哺乳动物视网膜神经环路的精细研究著称,如今竟有健康领域的科普作品问世,实属始料未及,乃忙不及迭,漏夜一睹为快。 读后方才明白,我的这位美国同行确实对健康问题有理论上的认真思考。他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概括来说就是,人类的各种生理功能(以指标显示其是否正常)和行为,固然有其细胞机制和分子机制,但总体上都受到大脑的调控。一言以蔽之:绝对是大脑说了算!而这种调控借助学习、记忆、文化、知识等完成,是一种主动的过程,其目标是对调控的力度作出预测,使机体能按需求作出迅速和适度的反应;如果功能和行为(特别是精神活动)的变化,超出了可调控的范围,人体就不再健康。他把这种稳态称为应变稳态(allostasis),即通过变化来达到稳态,这是对传统的内稳态调节概念的重大挑战。
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几乎都是为上述的理论假设做铺垫。他从一名患有遗忘综合征的青年的感知迷失谈起,介绍了在进化不同“纪元”,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的各种变化, 重点是第四个纪元智人大脑的特化和发育。然后他论述了进化对人类作出的“设计”必须强烈且高效,不然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大脑显示出对生理功能和行为越来越强的控制, 以至于到了侏罗纪哺乳动物出现时大脑对生理活动的调控开始起主导作用。作者随后引入了“应变稳态”的概念, 解释了这种稳态与传统的内稳态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尼安德特人大脑被按若干原则展开的惊人的发育。在这一章节,作者作为一名视觉研究的行家,展示了他对视觉如何快速扩张信号及神经计算的细致分析, 以及对知觉和运动控制的模块设计的诠释。经过这些知识的铺垫后,他对应变稳态的理论作了提纲挈领的归纳,并强调了他的这些观点对于解决健康问题的重要性。
通览全书,作者作为一名卓越的神经科学家,在论述中挥洒自如、旁征博引, 充分展现了他宽广的学术背景和对问题深刻的思考,他所提出的理论假设又正是他在青少年时期参与多种社会活动的背景的映射,于是这本书可以说生动体现了作者如何以严谨的科学事实为依据,为正确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背书,这一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他的这种高格调的对科学问题的分析,富有逻辑性的学者型叙述风格,使得阅读本书可能会是一场不轻松的挑战,而非闲暇时的消遣。 但是我相信,其结果必然会以知识上的满足和学识上的长进为奖赏。本书的这一特点也是对译者的功力的一场严格的考验。士刚教授的语言和学术功底都是我十分欣赏的,虽然他深藏不露,只是偶露“峥嵘”。在我记忆中,他第一次显示其才华是2015年在乌镇举行的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上,第二次就是他对本书的出色的翻译,他译文正确(“信”)、流畅当无可置疑,在“达”“雅”等方面也可圈可点,尽管有些段落的译文书卷气似乎略重了一点,不过,这浓重的书卷气却正体现了作者特殊的风格。
“何谓健康”,至今未有定论;各抒己见,正是学术繁荣之本。我毫不怀疑, 将会有一群高学历、高水平的学人成为本书的拥趸,从而使作者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特别是医学界更多的关注。
承士刚教授雅嘱,是为序。
杨雄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2024 年 3 月于上海
中文版序2
本书的作者彼得·斯特林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但他可不是你平常见到的那种美国神经科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文化背景是犹太人,心里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本书也不是那种普通的神经科学论著,而是一位终生关注社会运动的神经科学家对人类精神健康的深刻反思。
彼得和我的师生情谊已经近30年了。第一次见到彼得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时,选了他主讲的课程“结构神经科学”。结果发现,这门课其实是讲神经解剖学的。课程内容包括在利迪实验楼(Leidy Labs)地下室里,闻着气味浓烈的福尔马林解剖人和其他动物的脑子,还要背诵许多枯燥的解剖学术语。不过,整个课程有趣得多,彼得会不停地向学生提问,这些问题不仅像我这样心理学背景的学生回答不上来,连生物学背景的同学也常常答不出来。比如,他会问我们,一个突触小泡里有多少神经递质分子,释放后有多少能有效激活突触后受体?这些问题,我后来成为教授时在课堂上也经常问学生,国内的年轻学生也基本回答不上来。
很多时候,我们读教科书,以为自己懂了,实际上还有太多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懂,甚至连问都没想到去问。
当时我对神经计算很感兴趣,但上了彼得的课后发现自己对神经系统一无所知,就问彼得能否去他的实验室轮转一下。“热烈欢迎,你先来我办公室聊聊。”尽管彼得以他的应变稳态理论而闻名,但他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视网膜上。当我走进他在约翰·摩根楼地下室的办公室时,他首先非常自豪地给我展示了他在本科时参加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被逮捕入狱的照片,然后才开始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我在彼得实验室的轮转是由当时的助理教授濮鸣亮博士带领的,他后来回国在北京大学做了教授。濮老师教我做单细胞标记,通过共聚焦显微镜观察ON/OFF 亚型的α细胞和β细胞的三维形态学差异。在激动地标记了几十个细胞后,我觉得形态学研究开始变得枯燥乏味。彼得注意到了这一点,给了我一本书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禅与射箭的艺术》)。这种强调勤学苦练,最终技术达到出神入化的东方哲学,与我最初去美国学习科学前沿的愿望大相径庭。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离开彼得实验室,去神经电生理学实验室看看。由于彼得希望我留在他的实验室做博士论文,我本以为告诉他我要换实验室他会跳起来,但他只是平静地说:“我的实验室其实也有助理教授研究神经电生理和神经计算。”我鼓起勇气回答:“我不想再花时间在视网膜上了,想探索一下更高级的系统。”出乎我的意料,彼得没有生气,反而开始和我讨论其他可能符合我研究兴趣的实验室。
最后他说:“欢迎常来,我永远有时间和你聊天。”我后来在佩克尔(David Perkel)实验室做博士论文,研究鸟鸣系统的电生理特点,并请彼得担任我的论文指导小组委员。我经常找时间去他那里聊聊天,偶尔还有机会参加他家的派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两次谈话是,一次他拿起一期《时代》(Times),封面是上海铺天盖地的起重机,他说:“你以后应该回中国去。”这句话让我意识到,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去了美国都希望留下来,但其实回国发展也是一种选择。
另外一次,我因家里经济实在困难,需要做两份额外工作补贴家用。彼得看到我因长期睡眠不足而显得非常疲惫,便问起原因。我坦白相告,并告诉他,计算机系的同学帮我找了一份收入是我奖学金8倍的工作,为了养家,我可能需要放弃心爱的学术生涯。他问:“你现在需要多少钱才能熬过去?”我回答说需要3000美元。“你明天来我办公室,我来帮你。”第二天,他给了我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这笔钱一直到我博士后第二年才还给他。收到我寄给他的还款支票后,他在电子邮件里说:“我本来没指望你能还这笔钱,这样也好,我可以帮助其他人。”
事实上,彼得以各种方式帮助了不少学生,包括好几个中国留学生。他退休后,和太太萨莉(Sally,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系教授,曾是系主任)在巴拿马买了一个柑橘农场,所有收益都给了农场工人和附近的居民。显然,他受到都是美国共产党人的父母影响,是名副其实的。
2004年我回国工作前,开车8小时带着家人去给他和师母萨莉告别。之后我们也时常通过邮件保持联系。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5年,他和萨莉退休时正好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在树林中散步长谈时,我提到转向研究抑郁症,希望能更准确地理解治疗该病的神经环路机制并找到更好的疗法。
“我觉得你的思路是错的,”他说,“抑郁症归根到底是社会的问题,找新药物不是出路。”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谈话中充满了不同的观点。我坚信新疗法的重要性,并带着一丝嘲讽开玩笑说:“我知道你想继续推销你的应变稳态理论。”
虽然我当时嘴硬,但和彼得的最后一次深入交谈让我不断思考许多精神疾病背后的社会因素。在本书中,彼得从进化的角度宏观描述了动物神经系统如何积极主动地调整以适应环境,而不是被动地维持机体稳态。例如,我们通常认为人类的体温维持在37 ℃,但这种简化的观点几乎是错误的。首先,实际上我们的体温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有昼夜差异,并会根据特定的压力或情境发生变化;其次,这种调整是全面的,涉及全身多个器官的应变;最后,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通过增减衣物等方式主动调节体温。推而广之,人类的各种生理指标和行为都受到大脑基于学习、记忆、文化、知识等因素的影响,被积极主动地调控。而许多精神疾病,也许是超出了脑应变稳态的调节能力导致的。
彼得提到的美国社会“绝望之死”,包括自杀、毒品成瘾、卒中、肥胖等健康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而是人类社会现在及将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他强调,人类大脑更多地适应于进化过程中的狩猎采集(或曰狩猎采摘)生活方式,需要紧密的人际交流、社会合作、大量运动和频繁且不可预期的小奖励。然而,近几十年来社会组织和产业模式的急剧变化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减少了人际交往的机会,并使人们更容易获得大量非天然的奖励(如毒品),导致多种精神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他对背后的神经机制的描述(比如对多巴胺系统的简化描述)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他对进化的宏观视角仍然令人耳目一新。新技术不断快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例如如今大部分人通过手机获得主要的奖励和快感,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人类的精神健康,以及我们现代人需要如何在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进行调整,都值得深思。
回想起来,我非常幸运能从多位导师那里获得宝贵的指导。我的研究生导师佩克尔强调科研需要扎实,我的博士后导师卡茨(Larry Katz)则特别在意创新的重要性。但是,也许连彼得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他作为一位授课和轮转老师,会对一位成长于遥远中国山村的学生产生终生的影响。他不仅强调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还鼓励我们进行宏观思考(think big)。在近30年的交往中,他让我意识到学习和提高的空间永远存在。我期待本书的读者也能享受彼得对人类健康问题的独特视角,并从中启发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罗敏敏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新基石研究员
2024年3月于北京
001 — 前言
007 — 致谢
001 — 引言 迷失的水手
015 — 第一章 高效设计的基础:最初的30亿年
039 — 第二章 站在蠕虫的肩头
059 — 第三章 逃出侏罗纪公园
083 — 第四章 接踵尼安德特人
113 — 第五章 哪里出了问题
140 — 第六章 何谓健康
171 — 第七章 总结和结论
183 — 图片来源
188 — 注释
219 — 译后记
¥ 88.00
¥ 64.00
¥ 45.00
¥ 45.00
¥ 98.00
¥ 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