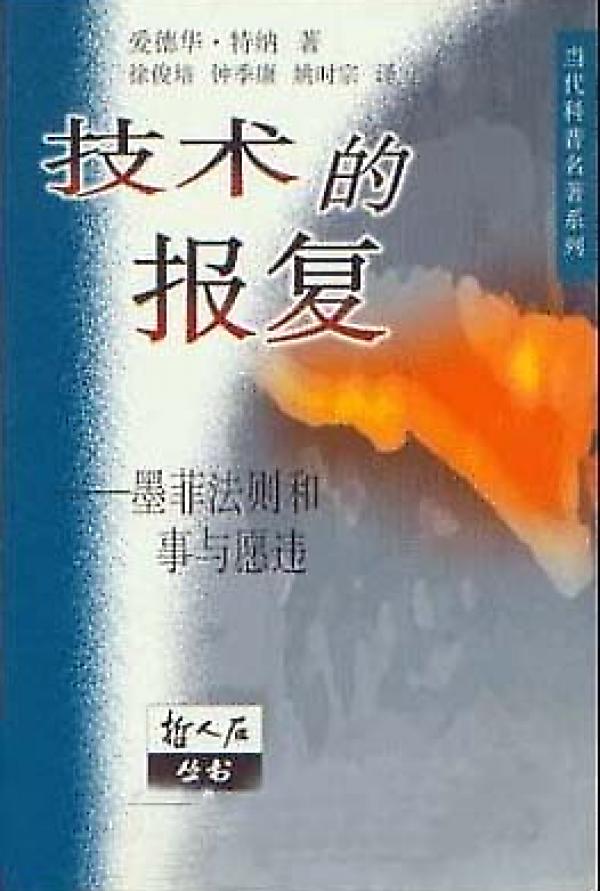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从事一种广泛的古代文明研究,涉及的基本问题既有智力上的也有道德上的,我们今天仍继续面对这些问题。他关注的是,我们能在这样的研究中学到些什么。
对于异域的信仰体系,我们能获得多大程度上的理解?对于古代世界的“科学”或它的各个组成学科,如“天文学”、“地理学”、“解剖学”等,谈论它们有没有意义?逻辑及其规律是普适的吗?存在一个本体论(一个单一世界)吗?所有尝试的理解都应该被认为是指向它的吗?当我们遇到明显不同的实在观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需要解释或可作为一种解释的概念间的差异?或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不同的首选推理模式或研究风格?真理和信仰的观念代表了可靠的跨文化普适的东西吗?
此外,对于当今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古代历史能教给我们什么?人性和人权的论述是普适的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帮助确保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和公正?
劳埃德将着手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使我们确信: 古代希腊和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为推进现代的各种相关争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第一章 理解古代社会
第二章 古代文明中的科学?
第三章 开拓疆域
第四章 一种共同逻辑?
第五章 探索真理
第六章 信仰的可疑性
第七章 研究风格和共同本体论问题
第八章 分类的使用和滥用
第九章 对实例论证的支持和反对
第十章 大学:它们的历史和责任
第十一章 人性和人权
第十二章 对民主的一种批判
结论
序
在我研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从事古代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古希腊和最近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我试图弄明白他们的世界观,它们为什么会呈现为那种形式,它们如何发生改变,而且为什么发生改变。我的主要研究大致属于古代科学史的范畴。但是受到我在剑桥大学所受教育的影响,并受惠于我早年与该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的学者如赫西(Mary Hesse)和布赫达尔(Gerd Buchdahl)等人的交往,我总是认为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分开是无意义的,试图脱离科学史来研究科学哲学也是行不通的。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哲学的考虑分为两种方式,首先是古代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但不全部是希腊科学哲学;其次是现代哲学名义下的科学哲学,包括科学是什么、各种标签的“实在论”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争论、真理的分析等等,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本书准备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要比我先前更为直接地面对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研究古代文明中的科学意味着什么?并通过这么做来为现代哲学争论作出一些贡献。第二件事是,也比我以前更为明晰地思考: 古代历史如何能对当今世界一些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产生有利影响。
在第一件事的名目下,我在此罗列出如〖〗序下这些问题: 对古代社会,我们能获得多大程度上的理解?对于古代世界的“科学”或其各个组成学科如“天文学”、“地理学”、“解剖学”等,是否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它们?逻辑及其规律是普适的,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或者必定是)真的?存在一个所有尝试的理解都应该指向的本体论——单一的世界吗?真理和信仰的观念代表了可靠的跨文化普适的东西吗?
对上述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不会是简单的是或否,而是要先对有关问题做出澄清,并移除困扰着有关讨论中的各种疑惑之处。这些澄清实际上能对当前的哲学争论产生影响,因为无论科学实践已经发生多大的改变,实际上古人努力探索的历史仍在为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提供相关的材料。不同年代和地域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接受和承认这种多样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去探讨他们的不同研究风格(styles)。研究风格是我从克龙比(Crombie)和哈金(Hacking)那里借鉴过来并做过修改的一个概念。本书中两个最为详细的研究个案出现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主要关注因对分类(classification)和实例论证(exemplification)的不同兴趣和不同运用而构成的不同研究风格。研究风格显然受限于与艺术风格、文学风格或甚至哲学探讨风格不同的约束条件。但是这个概念有助于正确地判断所讨论的不同研究有一些什么共同之处——这些研究归根结底指向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阐明的一种共同主题——以及不同在哪里、为什么不同等。
在第二件事的名目之下,即针对当今的问题,我们能够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在本书中提供了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与高等教育有关——现今大学的角色和它们的未来责任。第二个案例涉及人权和人性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第三个案例关系到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民主制度的力量和缺陷,尤其是后者。
在开始进行这些研究之前,我应该先列出指导我的方法论的四条主要假设,虽然这些假设需要在特别的行文语境中加以详细阐述。我的第一条方法论原则是,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应尽可能使用参与者的而不是观察者的范畴。我们当然不是要把我们的先入之见和期待强加给古人。相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力把握古代研究者自己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工作、理念、目标和方法。然而,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贯彻这条原则将会遇到一些困难,并带来其自身的哲学问题。尽管如此,复原古代思想观念的雄心既是我的方法论基石,也是它的战略目标之一。
我的第二条方法论原则是,我支持这样一个信念,即在科学中不存在与理论无关的观察,在科学史上不存在与理论无关的描述。对于后一种情形,把理论先见搞清楚显得更为重要。认识到观察描述中的理论和价值判断无法避免,当然并不等于说,我们在研究中可以采用任何基本概念框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更为小心谨慎地考察这些成见和偏爱,无论它们是否直接源自某些现代预设。此外,我们能够、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能觉察到的理论负载(theoryladenness)程度上的差异,尽管在最小限度上仍旧不会有无理论负载的陈述。
我的第三条方法论原则是,我们不能期望在科学或科学史研究中有最后确定的答案。所有的结论都处在待修正状态中,虽然有一些结论,尤其是在科学中,显然比其他一些结论更为强健有力。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去检验和评估各种理论和解释。总还是存在着一些行得通的客观性(objectivity)、真理(truth)和真相担保(warranting)的概念,即使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产生出绝对、确定的结果。
我的第四条方法论原则来自我对字面/隐喻两分法(literal/metaphorical dichotomy)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我确信使用这种两分法是十分危险的。单义性(univocity)是一种很局限的情形,不能指望绝大多数词汇能够遵守这一条准则。反之,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个词汇都能展示出一定程度的我称之为的语义延伸(semantic stretch)。但是,这非但没有加重诸如翻译中的不确定性之类的问题,我们反而能够看到,这使得我们能在不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个人习语的相互解释之间建立一种连贯性。
对那些习惯了老式的实证主义问题解决方案的人来说,这四条方法论原则似乎为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基础。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为这种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它们使我们能够仔细推敲那些跨越不同古代学科的不同古代研究者,对相同现象或者也可能是不同现象的认识。这能帮助我们避免大量实在论和相对主义或建构主义立场之间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也有助于避免把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和真理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作为两个独立完全选项对立起来的僵局;还能使我们避免过度使用不同信仰体系之不可通约性的强命题。我应该强调,在不同的智力探索、科学、哲学和历史中,我们能够为证明和辩护事物真相确定恰当的标准。这些标准永远不可能是最后确定的,而总是在等待修正(方法论原则3): 但是它们足以做出暂时的判断,这是我们唯一能指望做出的一类判断。对确定性、不容置疑性和不可纠正性的需求,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起源,就像我们对字面和隐喻间的两分法所做的同样的事,而我们能够看清它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发展的偶然性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解脱这样的束缚,即在任何基础牢固的研究中,都要把它们作为必需的要素加以考虑。
在本书中展开的一些思想来源于我在世界各地、在不同时间用不同的自然语言所做的一些讨论会报告和演讲,它们也要归功于在那些场合中听众们所提出的建设性批评意见,还有来自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古典系和李约瑟研究所同行们的宝贵意见。我很高兴也应当向他们表达谢意,同时我也向那些友好地同意我发表我报告的较早版本的编辑表达我的谢意。
第一章源自我参加的一次探讨“解读中的宽容原则”若干问题的学术会议,该次会议由德尔普拉(Isabelle Delpla)组织,于1998年11月在法国南锡召开。本章的一些想法包含在一篇题为“解读中的不宽容现象评述”(Comment ne pas être charitable dans linterprétation)的文章中,该文收录于该次会议的论文集(Delpla 2002)中。
第二章主要归功于1999年我在英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题为“关于科学的‘起源’”(On the “origins” of science)的演讲。后来受到刘钝的邀请,2001年9月我作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在北京作了另一个版本的同名演讲。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我在迪布纳科学史研究所一次关于中国科学的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要点,该次会议由林力娜(Karine Chemla)和金永植(Kim Yungsik)组织,于2001年11月召开。本章部分内容又收录于出版于该年的意大利语百科全书《科学史》(Storia della scienza)第ⅱ卷第Ⅰ章。
第四章和第七章中的一些论点在2000年9月由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罗森(Jessica Rawson)组织的题为“中国和西方: 一个还是两个世界?”(China and the West: One world or Two?)的会议上首次提出。
第五章论述的问题源自2001年10月我在法兰西学院参加的关于“科学中的真理”(La Vérité dans les sciences)的一个讨论会。我的报告的法语版本由珍妮特·劳埃德(Janet Lloyd)翻译,收录于由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和布弗雷斯(Jacques Bouveresse)主编的该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中。
第六章进一步发挥了2002年7月我在里斯本参加的关于“信仰过程”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点,该次会议由吉尔(Fernando Gil)组织,会议论文集正在出版中。
第八章详细阐述了1997年4月我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马雷特讲座(Marett lecture)中提出的论点,该演讲即将面世[由奥尔森(Olson)主编]。
第九章展开的材料来自我给《远东远西》(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1997年的一期专号的一篇稿子,该文讨论中国思想中的实例论证,该期专号由林力娜主编。
第十章源自我所作的一篇演讲,该演讲分别于2002年2月由悉尼语法学校的瓦兰斯(John Vallance)和2002年10月由日本仙台东北大学的加藤守通(Kato Morimichi)主办。
第十一章来自2000年11月由伦敦历史研究所的卡纳丁(David Cannadine)组织的一个关于人性的系列研讨会上的报告。
最后的第十二章进一步阐明了我在一篇被收录于《思考的风格》(Le Style de la pensée,Paris, 2002)一书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该书是专门献给不伦瑞克(Jacques Brunschwig)的纪念文集。
我要感谢上述所有场合的主办者或组织者们和我的听众们,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阅人,感谢他们提出有益的和建设性的意见,而按照一如既往的惯例,他们无须为本书的最后结果承担任何责任。
G·E·R·劳埃德